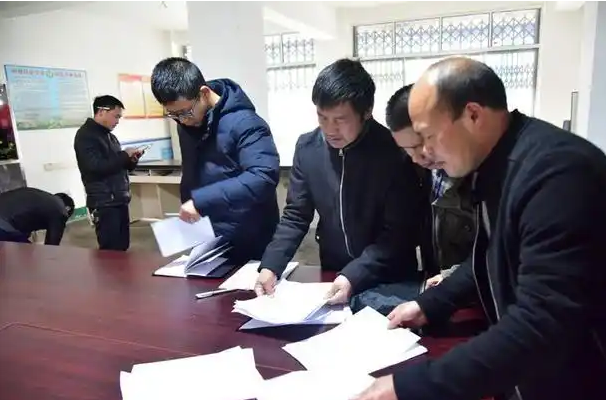本文选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 2023)
在中国历史上,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实在太少了。他这样的人,即使出现,也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众人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19世纪西力东侵,欧美人挟其坚船利炮以及商业资本,打开亚洲的门户,其势如惊涛骇浪,莫之能御。
亚洲国家仓猝应变,无论在武备与心理上均不足以应付此一史无前例的巨变。
今日回顾历史,东亚二国——中国与日本——虽同在外力侵逼下起而应变,日本的应变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中国。咸同中兴尚在明治维新之前,然而明治维新三四十年后跻日本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同光自强运动三四十年后却是甲午惨败以及庚子国变。
中、日同被西方势力逼向世界,追求富强。日本的成功,更衬现中国挫败之甚。
无论成败,各有原因可说。德川日本虽然锁国二百余年,但兰学一线从未中断,故明治之前西学已有基础。而其封建制度亦有利于应变,如德川幕府应变不利,而长门、萨摩诸藩应变较顺,卒于美国兵舰示威江户湾,受辱之余,发动尊皇攘夷的倒幕运动,明治皇帝收还版籍,中央一统,开创了明治维新,走向世界的新局。
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西洋教士虽早于明末来华,然自雍正禁教之后,中西文化实已隔绝,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甚浮浅,而满清中央集权颟预无能,既难应变,又无可资应变的地方势力。太平天国之起,固无助于应变,内乱更助长外患。
所谓同治中兴,实在有名无实,无论宗旨与规模,全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中、日之间一败一成,诚非无故。
郭嵩焘一再感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不明洋情,不知如何应付洋人,以致于屡次延误,使洋务既愈来愈难办,国家也愈来愈艰危。这也就是说,中国应变愈早,自强的胜算愈大;不仅仅是因中国的国势日诎,而且是因列强的侵略性日增。这个“时机”问题,颇值得一究。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鸦片战后五六年),欧洲革命导致三十三年西方旧秩序的解体;革命虽不成功,但列强必须重组均势。
洪秀全金田起义时,英国仍是唯一的世界性工业国,法国的工业力尚限于欧陆,俄国尚落后,美国更不足道,日本仍在闭关,而中国正遭遇到空前的内乱,坐失应变自强的良机。
同治中兴尚未为晚,但力已不从心,见识亦不够。及光绪初年以后,德国崛起,危及均势,引发列强争霸,英、法、德、俄诸国分向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以充实一己的资源与声威。日本约同此时维新,效法列强,不仅免于受害,反而有余力伙同西洋侵略,而中国正适当其冲。
郭嵩焘出使英、法时,颇注意俄土战争,知道西方列强中,英法为友邦,德俄为友邦;回国途中更忧虑日本之起,类此都可见他对世界形势有基本的认识。他还注意到柏林会议,此一会议的结果又暂时恢复了列强的均势与国际间的和平。但郭氏回国后竟投闲置散,对世界的看法亦不被决策者重视,清廷的应变仍然无方,还想与霸权力拼,以至于藩邦与利权的大量丧失,而无可奈何。
于郭嵩焘逝世前后,中国即将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正亟力奔走呼号变法。变法之紧急,正可见国家之危急,已到崩溃的边缘。
然中国之所以如此,论者每归咎于以天朝自居的政治立场,以及文化大一统概念下的拒外观点;而又以此政治与文化观点,来自两千余年的儒家传统。传统阻碍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能并存之说,遂甚嚣尘上,认为非彻底打倒传统,全盘西化,中国不足以言现代化。此种议论自“五四”以来,余波荡漾,迄今未竭。
但是近三十余年来,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现传统与现代化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传统因素颇有助现代化的发展。就以日本而论,如德川时代儒学中的伦理价值,对于日本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大有助益。同一儒家传统何以有助于日本,而有碍于中国?两国政治社会环境不同,自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可探,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仅以传统与文化为说,已显得空泛不实。
郭嵩焘生长于此一挫折时代,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对国家与人民的遭遇特为敏感,而且慧眼独具。我们不妨从他的眼光来探看此一问题。无论他的出身与教育,都属当时的主流。他亦以儒学自任,并对礼学有深入的研究。尽管许多保守派将他视为离经叛道之人,但他从未自认为儒家叛徒,事实上亦从未向儒学挑战。至少深厚的儒家背景并未阻碍他认识西方,走向世界。在他看来,主要障碍是南宋以来虚骄的士风。南宋以来的士大夫阶层,固然大都信奉儒教,但虚骄之气显然是一种社会风气,未必扎根于儒家经典。风气之形成,有其时代背景。自两宋以后,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关系日形密切;元、清两朝,即由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兴建。
士大夫高唱夷夏之辨,引发情绪性的反应,一反汉唐时讲究理(接之以礼)、势(备而守之)的政策,而“务为夸诞”,竟侈言用兵于靖康、绍兴积弱之后。郭氏指出,史家班固曾说,文人多主和亲,武人则多主征伐,但宋、明以来,言战者却大都出于文人,议论繁多而不切实际,甚至轻易开启衅端,使曲在我而不在彼。所以他撰写《绥边征实》一书,以检讨从秦汉到明代的“边防战守之宜”,突现其得失成败,以明“兴衰治乱之大原”、“砭南宋以后虚文无实之弊”。惜《绥边征实》书稿未出,仅存序文。
郭写此书,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杨联陛指出,郭嵩焘从未把洋人比作牲畜;古人将夷狄视若牲畜,因夷狄野蛮而无文明,其实郭氏认为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杨氏又说郭氏主张传统的羁縻政策,其实郭氏曾一再明言,洋人绝非传统的夷狄之比,西洋文明固高,其各国之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不似旧时夷狄的狼奔豕突,是以他有“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之说。
情势既然大异,古代的政策无论攻伐与羁縻,都不足有为。他之所以要征实过去的绥边政策,正欲揭出南宋以来的虚骄士风。那种虚骄在宋、明时代,已足招祸,何况与坚船利炮的洋人对抗?势必每下愈况。
然而他亲见的士风,其虚骄较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明弓箭不敌枪炮,在朝的官吏、在野的士大夫仍然轻易言战,而郭之剀切避战之论则被视为大逆不道。郭氏逐步发现好战与排外的士论并非单纯的忠愤之气,且兼有迎合当时国人因列强侵略而导致的仇外心理,以自鸣高,以博取时誉。
且不惜动用一切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诸如春秋大义、华夷之分、君父之仇、国体等等,以气势慑人,压制理势(郭氏特别强调理势),甚至挟制朝廷,影响决策。
似乎是传统文化在作祟,其实是虚骄之辈利用了传统文化。这种虚骄,既不明理势,亦不讲是非,甚至只为了个人的名利,在郭氏看来,真可说是具有叵测的居心。
在此又牵涉到一般官吏与士大夫的品质问题。他们在郭嵩焘眼中,只能代表传统中国的衰落,正可与当时日见败坏的吏治相印证。他因而颇怀念康乾盛世,哀伤道咸以降的式微。他接触甚广,自感衰世的景象触目皆是,最具体的表现,乃是整个风俗的堕落。郭氏所谓风俗,与人心是紧密相系的。人心变得险诈、自私、不明是非,蔚然成为社会风气,便会影响风俗的纯正。风俗是整体的,一旦败坏,官贪民穷,盗贼四起,社会上一片乱象,又何以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巨变?
郭嵩焘被称为洋务派。的确,他对于洋务的识见高人一等,但他对“内务”更洞若观火。当时的保守派耻谈洋务,洋务派忽视内政,而郭氏不仅将洋务与内政连接起来,而且认为内政若不能整顿与振作,花力气搞洋务亦是枉然。他赞同知交良友刘蓉所谓:“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
他晚年愈来愈感到悲观,即有鉴于人民风俗日恶,吏治益坏,百姓愈贫之故。换言之,自强大业要由烂摊子来撑,无论如何是撑不起来的。就此而论,以郭氏之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除因对西方世界认识不足外,更由于传统政体与社会之衰弱,以致无力应变。言及无力应变,李鸿章于复郭嵩焘函中提供了最显明的证词:
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于是年冬底赴京师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连垂帘听政的太后以及恭亲王都无办法,可见传统政治中的腐败力量已达到足以扼制改变以求自存的地步,而所谓阻力,乃系传统中的腐败力量,而非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挫折亦因而是双重的。
内部的腐败与对外的无知又互为因果,虚骄很容易一泄无遗,成为泄气,清流如张佩纶诸辈于中法战争前后的表现可为明证。这些士大夫“始则视之(洋人)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实情”。而仇外与排外亦很容易转化为惧外与媚外,因同属无知的情绪化表现,郭嵩焘亲眼目击平昔排外的总督瑞麟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可借此一叶而知秋。郭氏肯定甚至赞美西洋文明的言论,固易被本国人斥为媚外,其实颇具胆识。我们从郭氏一生可知,他冒大不韪向国人称道西洋,原想要国人认清西洋,以知彼知己;而与洋人交涉时却表现得不惧不媚,且常据理力争。
无论据理力争或赞美外国都出之于理性,正好与出于情绪化的言行恰恰相反。他一再要求国人循理,但国人一直无法摆脱情结的纠缠。走向世界之路,亦就步步荆棘。
郭之循理思想主要来自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教育的影响,足见传统其一,用之迥异而已。郭之生平际遇自有助于其识见,他亲身体验到鸦片战争,洞察西洋的坚船利炮,及见洋人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乃警觉到大变局的来临。所谓变局,就是通商之局。中国正宜迎合此局而谋求自强,不应以力拒之,实亦无力拒之。是以他早于咸丰年间即已获致“战无了局”的结论。他一意主和,引起当时以及后世的误解最多,甚至被讥为怯懦的投降主义者。但是主战的结果又如何?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越南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只有使中国损失更重,屈辱更深,尚需割地赔款。郭嵩焘并非不知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并不想轻易开启战端,中国正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紧握自强的时机。
此种考虑确是很理性的,但是由于外国侵略在中国所产生的激情,很难接受理智的引导,而郭氏生平的逆遇即多与此有关。
郭嵩焘同时代人中,当然还有一些颇能以理智看清时局者,认为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如年龄较长的冯桂芬,同辈中的王韬、郑观应,以及晚辈严复,都能洞悉西洋长处。王、郑、严等见解较郭尤为激进,但由于人微言轻,在当时并未受到注意,王、郑尤被视为通商口岸的“边民”(marginal men),自远不如兵部侍郎以及驻英法公使之一言一行,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因重视而受到强烈的抨击,在当时可说独无仅有,几难于自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亦正见其在当时的一点影响力;反弹的强度应与冲击的强度成正比!从长远看,中国终于走向世界,郭氏所发的一点冲击,应多少有些贡献。
郭嵩焘同时的政府中人,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均以洋务见称,官位甚至比郭更大,影响力比郭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的洋务仅止于坚船利炮的自强,一意欲以洋枪洋炮来巩固既有体制。郭则进一步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并且批评到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深处。
他又不避赞美西方之讳,而且择善固执,于私函中自谓,虽“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因自觉“所犯以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于此可见李、沈、丁辈虽亦遭世诟骂,远不如郭之甚,并非偶然。而郭氏执着之深,正见其信心之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
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至于被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
其实他一生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与曾国藩、左宗棠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得到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奕䜣的赏识。但这些关系,由于他的思想与个性,对他没有多大的帮助,左宗棠更极力相倾。至于一挫于僧格林沁,二挫于毛鸿宾,三挫于刘锡鸿,更与他的思想与个性有关。
唯一欣赏他而且想帮助他的是李鸿章,但即使以鸿章之显赫,亦有爱莫能助之憾,无法用其才,只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总之,郭嵩焘作为一挽澜者,不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以去。今日过了一个世纪,寻看古人遗迹,不能不欣赏这个当时的弄潮儿。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