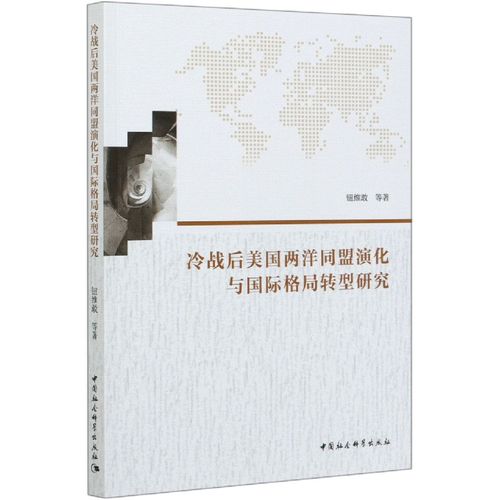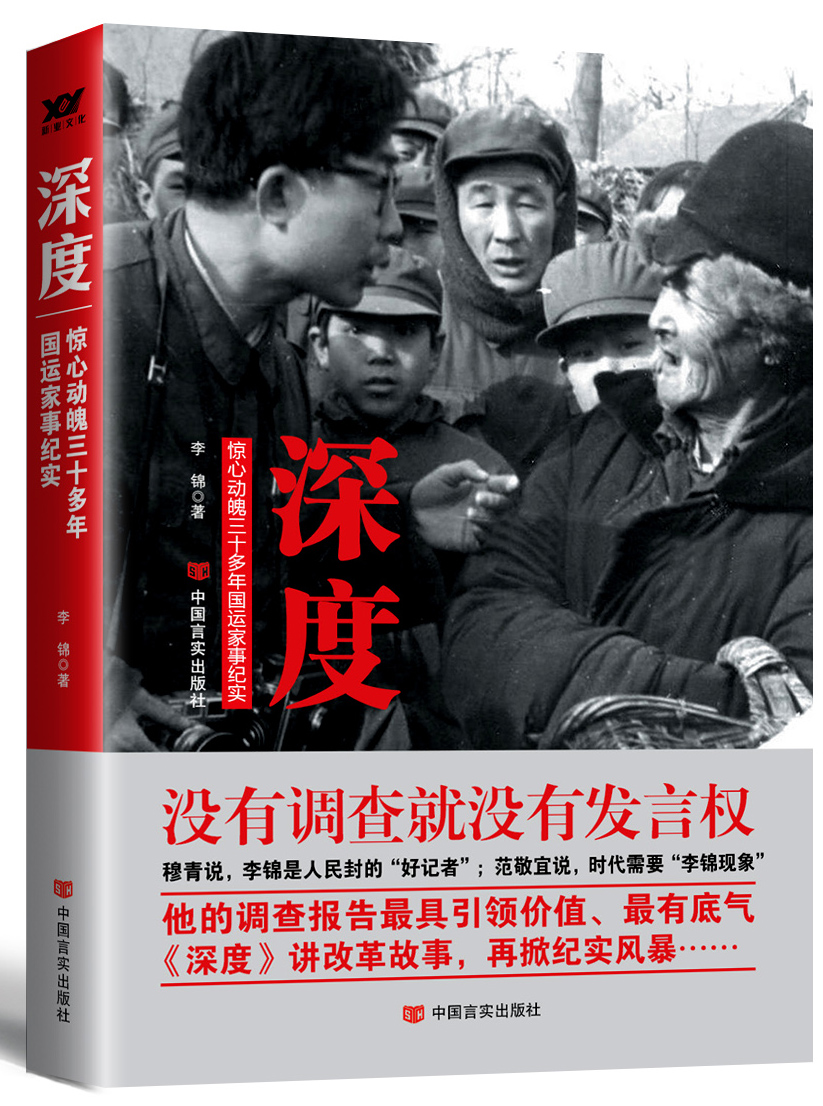作为NHK电视台资深记者的采访手记,《无缘社会》以由此及彼倒逼追问的方式聚焦“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问题。它不仅仅是对采访过程的还原,更想回答的是以下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失去与社会的关联而成为“无缘死者”(即孑然一身死去之后无人认领遗体的逝者)?这些关联与纽带又是如何在人生中失去的?日本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水面下究竟发生着什么?
书中的 “无缘社会”,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关联的社会,各不相干的社会”(《序言》第2页)。这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与社会的必然衔接已经淡化到几乎可以忽略。今天的日本已经表现出了“无缘社会”的一些较为严重的症状,包括单身成风、老人独居、故乡消失、职场缘浅。
“无缘社会”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则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永恒话题。它们不仅在涂尔干和韦伯的经典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且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依然是焦点所在。书中所关注的“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问题,以及“无缘社会”的种种肇因,均可以在鲍曼(Bauman)、贝克(Beck)、吉登斯(Giddens)这三位当代社会学大家所提出的“社会个体化”命题中找到解答。具体来说,导致现代社会“无缘死者”不断增加,“无缘社会”加速到来的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个是贝克所说的“脱嵌”(disembedment)或吉登斯所指的“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即个体日益从血缘、地缘、学缘和业缘之类的社会纽带和约束中脱离出来,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原子化。
从前的日本社会,“人为了不陷入孤立无援,为了不被周围的人排斥,对亲戚也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和邻里也尽量打成一片。”也就是说,那时的个体深深嵌入到家庭和亲属关系,以及职业网络之中,并为它们所界定。然而今天的“樱花之国”,“脱嵌”大潮汹涌澎湃,其中一个后果便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和获得个体自由的同时,失去了既往的各种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的支持。慢慢地,整个社会也逐渐从传统的“有缘社会”变成了当下的“无缘社会”。
第二个原因便是鲍曼所指的“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这种十分吊诡的现象。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结构强迫人们成为积极主动和自己做主的个体,对自己的问题负起全部责任,发展一种自(我)反(思)性的自我。
这一进程是通过诸如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监管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来实现的。通过减少人们寻求传统、家庭或社区之保护的各种选择,现代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事实上在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在《无缘社会》一书中不断地听到,“我不想为了自己的事再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页2)、“要说死的话,我倒情愿一下子悄悄地死掉,给谁也不添麻烦”、“就算有孩子,我也不愿意给他添麻烦”(页46)这样的喃喃自语。在这里“强迫与义务的自主”偏执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所反问的“所谓‘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相互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页2)至于社会制度对个体的不断增加的影响,日本“失落的一代”的独白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到三十五岁,转折就出现了。在结婚市场上,这个年龄也就意味着人开始贬值。”(页182)“我周围的独身男子也说因为收入不稳定,没法结婚。”(页187)孤独老死者接收机制的创立者,富山县高冈大法寺的栗原主持感慨道:“即使是我们,如果人生道路走错一步,生活中出了某种问题,说不定都会成为独居老人而悄然死去的。绝不是仅有某个特定群体的人才会孤独老死,他们也曾过像样的人生,或许也曾有过孩子,或许也曾把孩子培养成人,或许自己出生时也曾让爹妈喜出望外。他们都有各自走过的人生,怎么能仅仅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孤立了,就让他们的下场如此不堪呢?”(页62)然而,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高涨的现代人,不会因为一句“请重新融入社会”的劝告,就马上转换思维,着手建立和社会的关联。大部分人心里想的恐怕依然是“请不要干涉我的自由”。这也就意味着,很大程度上,“强迫与义务的自主”以及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的高涨,和“无缘死”、“无缘社会”,其实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事物罢了。这其中的悖论与吊诡或许正是物质相对丰裕的现代社会的宿命。
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国度,通常在日本流行的,慢慢也会流传到紧随其后的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因此同样的情况在韩国、中国的台湾已经发生了。其实中国大陆也差不多,但没那么严重,因为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才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少子化、社会的个体化趋向一同发酵,中国社会似乎也会步上日本社会“无缘化”的后尘。因此,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不管是为了避免重蹈日本社会的覆辙,还是为了减少或对抗“无缘社会”所造成的痛苦,我们都应该认真阅读NHK所推出的这本具有强烈人文关怀、反思“无缘社会”的纪实作品。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