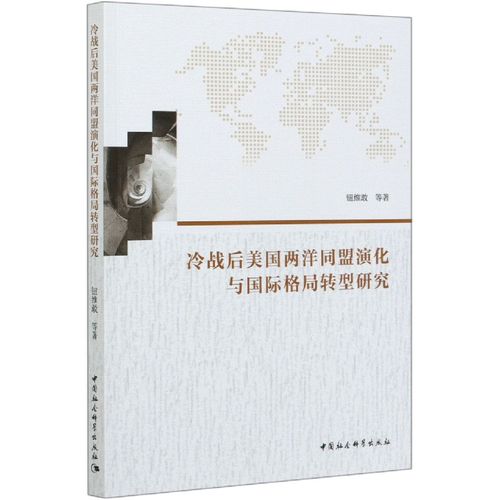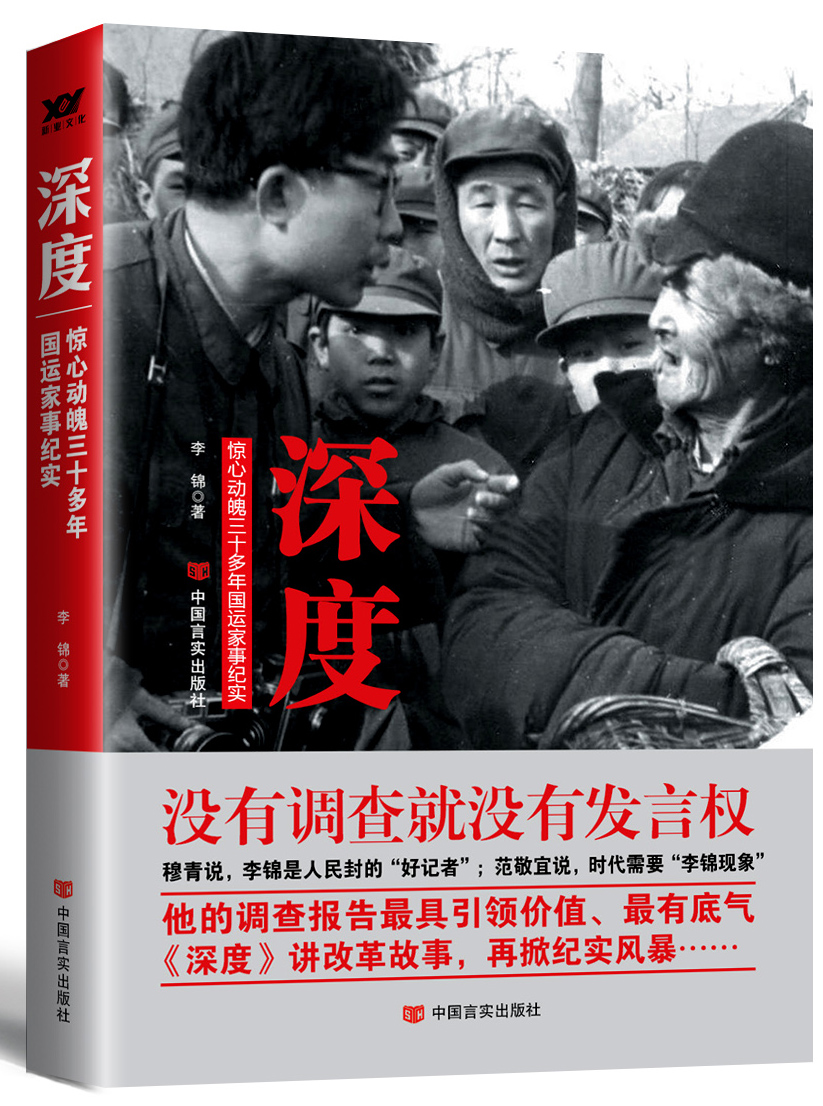周其仁的学者生涯是从研究农村开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调查研究农村改革。而他早岁下乡黑龙江,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研究和著述也影响重大。这些年来,周先生在公共空间里的姿态写照,是以言论介入现实,并且始终关注着农村。他的新著《城乡中国(上)》,便是他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很多地方城乡情况后的思考,从城乡角度解读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感极强。
在周先生眼中,中国虽然很大,但其实只有两块地方:城市,乡村;中国人口虽然很多,其实仅分为两部分:城里人,乡下人。“城市国家”是有的,譬如新加坡,“乡村国家”——整个国家全部由乡村组成,完全没有城市——不但当今没有,似乎很远久之前也没有。一个国家分为城乡两个世界,相当普遍。但城乡呈现出的两极发展格局,却有太多中国独有的因素。
《城乡中国(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城市的功用,集中于对中国目前城市化滞后的追问与思索。城市化进程,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但内容实在庞大,包罗万象,尤其要解决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尖锐问题。第二部分讨论阻碍城市化进程的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则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第三本部分讨论地权的演变路向,第四部分讨论主导机制的分叉,究竟是放权还是还权,改革出发的深层风险何在。第五部分,确权走新路。这部分内容应该视作本书的文眼所在,周其仁把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视为当下各类社会问题矛盾的焦点与根源。他的问题是,土地转包之后,我们的改革还能走多远?
先看一组对比数据。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17.9%;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52.57%。也就是说,34年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据预测,在未来的2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将提升至70%,与发达国家相当。而西方国家完成同样的历程,平均用了将近100年。迅速走向城市化的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资源向城市滚滚流动。新一届政府一再强调要加速城镇化进程,无疑会推动新一轮的人口迁移。
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和即将衍生多少矛盾和悲喜?中国城市化历程中的逻辑何在?周先生在书中发问。
首先是户籍问题。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为人诟病,其在实质上限制了“迁徙自由”。从现实看,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面对着重重困难,面对着一大堆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我们在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二十多年来数亿农民工进城打工,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民进入城市都是受到限制的,他们的身份是尴尬的。城市既需要他们,又排斥他们。现有的制度设计,使他们无法享受许多城市的公共服务,一来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理由,如果农民大量进城,那么就会降低农业产出。当然相较于自由原则而言,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在今天看来早已站不住脚。实际上,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也不一定能提高农业的产出。因为大量农民之间的激烈竞争会降低单个农户的收入水平。二来却是基于维护城市利益的理由,如果农民大量进城,就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福利。这个理由倒是和如今继续维护户籍制度的理由如出一辙。但这个理由却完全忽略了由于人口集聚带来的巨大收益和外部性。尤其是由于人口集聚催生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扩展。
其次是土地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向外蔓延,乡村建设面积也不断扩大,有限的耕地面积由此不断受到挤压。同时,由于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城市地价急速上升,与此同时却有大量农村非农用土地对相对价格的变动根本无法随之做出反应。2003年,成都开始土地改革,即把远离城市的那块“不值钱”的建设用地平整,复垦为农地,然后把原来可以用于建设的权利,抽出来“落到”靠近城市、城镇或中心村的位置,因为这些地方建设用地比较贵。对于土地改革的“成都经验”,周其仁的判断是:只要城市化引发的不同位置的土地之间有足够大的差价,那么在允许交易的条件下,低价位置的建设用地,就能位移到地价高的地方,而农地却可以从高地价位置位移到低地价的地方。周其仁认为,土地的高度集体化埋下了祸根,成都土地“位移”的过程,释放出一种经济能量,既支持了新农村建设,也支持了城市化。对此,周其仁建议,为改变城乡产权不对等症状、为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奠定基础,要抓紧推进土地确权、价格机制、配套市场和“最必要的管制”(目标是任何人行使他的权利的时候,不能损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等深层次改革。
周其仁认为,在中国城市化诸多矛盾现象的背后,有着难以阐释的逻辑:工业化发展不起来,城镇就给不了乡下人更多的机会和容纳空间,这好懂;可是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的大门却对始终对农村紧闭,却实在不好懂,难以解释。再有,人往高处走的动力学,好懂,所以工业化、城市化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不断从低收入的乡村地区移向机会与收入较高的城市,也好懂。从这个逻辑出发,城乡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强劲的进城移民运动,等到更多的农村移民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趋近。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这岂不是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这就在提醒国人,虽然三十多年来我国土地制度经过了多种演变,但集体化制度的残留仍顽强存在,而且今日的城里人和乡下人,每人的命运都仍时时、处处受到这种制度残留的拨弄,这正是至今中国仍在为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而苦恼的制度性原因。
所谓改革,是为了获取应有的权利。权利即正当性,没有正当性,就不是权利。权利和权力,都需要正常逻辑的校准。
读周其仁的文字从来都不轻松,他发现问题的敏捷与浓郁的现实关怀,以及进退有度的批判意识,都让他的文字显得清健理性,机警与厚实,有一种不屈不挠想要击中时代症结的努力。这种精神和毅力,在当下的学术界显得格外可贵。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