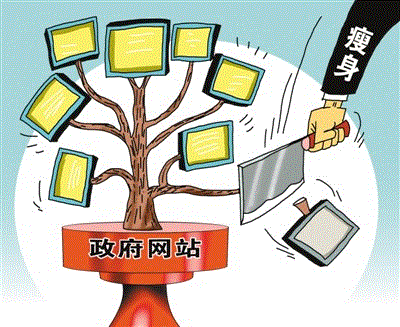推进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与盈利性经济活动相分离,打破村庄一级的“政社合一”体制,这对于防止隐蔽村霸产生有釜底抽薪之效。
近期国家部署了“打黑扫恶”专项行动,引起舆论高度关注。这项行动在农村具体体现在打击以“村霸”为代表的恶势力犯罪。另一方面,近年国家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倡导新乡贤的积极作用。把这两件事真正做好,需要对相关问题有一种相对深入的认识。
明火执仗的村霸不难对付
个别乡民干了一两件坏事很难成为村霸。典型的村霸成立的要件,一是其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劫财害命,破坏乡村公序良俗;二是其聚敛不义之财,罗织自己的经济组织;三是在公权部门培植保护伞,图谋长期发展,扩大势力;四是按黑社会原则组织自己的帮派。帮派团伙想要把一般的依附者发展成为核心成员,往往会有一个“仪式性”的活动,要该依附者干一件走上不归路的恶事。鉴于村霸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他们纠集成的团伙有时不一定具备上述全部特征。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政治集团拥有保证国家不失现代文明的执政能力,那种明火执仗的村霸也就不会有太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本没有能力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若一些地方因官场腐败等原因使其执政能力出了问题,村霸势力不免纵铸成山头,割据一方,形成瓦解政权的政治势力。有头脑的村霸在一定时候会“金盆洗手”,对自己控制的区域采用安民手法,而在更大的范围里玩起政治来。这种威胁不得不防。
农业文明时代发生国家政权被颠覆的情形,除异族入侵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王权内部的腐败逐步滋生蔓延,以致政府衰弱、纲纪废弛,乡村恶势力坐大,礼教不再能维系乡村秩序。于是,当兵成了活路,兵器成了饭碗,全社会乱成一锅粥。有人认为乡村自发的土地兼并导致政权更迭,其实是本末倒置之论。在农业效率低下、非农就业机会不充分情况下,农地交易的定价机制里有安身立命的生存性因素,会形成一种土地分配大体平等的安全机制,普通乡绅也难以触碰这个壁垒,只有和不法政府官员勾连的恶霸才敢于伸出脏手。所以说,对明火执仗的乡村恶霸,历代历朝都不待见,欲除之而后快。
二元结构下隐蔽矫饰的村霸更可怕
如果村霸就是明火执仗、舞枪弄棒的那种,倒不是太麻烦的事。真正难以忖度、且在实践中不好应对的是颜色不显、形象模糊的那一类乡村权威人物。这其中,有村霸存在当属无疑,只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比如,东部某市的一名村党委书记,曾经在地方上声名显赫。大约在20年前,他的村庄已经有了8亿元之上的工业产值。他依靠家族控制村庄——村庄的核心岗位均由其兄弟姊妹把持。但他把村庄经济弄得风生水起,自己得到了通常由政府给的很多头衔,村民也有得分红增收。此人后来被下了大狱,是因为有村民不再听话,找他家族的麻烦,他的势力便弄死了这位村民。
近年关于村霸的消息也屡见报端,可见上述案例不是少数,否则国家目前也不至于把解决村霸问题当做法治“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
我国当下出现的村霸除不同程度上有前述乡村恶势力的特点之外,他们还多在国家正式制度体系中有一定的位置,甚至捞取了一定的官方荣誉;在东窗事发之前,他们一般不会恶名昭彰,而能够把村里的反对力量摆平,把盖子捂住。他们的确有隐蔽性,甚至有鲜亮的颜色。
黑帮势力一般存在于边缘性社会,而农村社会在农业文明时期就是主流社会,在工业文明时期也不应该是黑帮势力喜欢染指的领域,那么中国当代社会却为什么村霸迭生?笔者以为,这种情形出现与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系统有关。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乡贤与村霸难简单区别
不妨设问,《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恶霸还是乡贤?依笔者看,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他大略算是乡贤;若在工业文明时代,他则有演化为村霸的可能。他在乡里维护礼教,同时也发展公益事业,在行使“皇权”代理职能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乡民利益,这是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比较标准的乡贤范式。
他干预已经萌生的乡民自由,竭力维护已经摇摇欲坠的礼教传统,控制村庄经济活动,若放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如若村庄受市场经济冲击,出现了新的致富机会,资源分配秩序需要重新调整,他在家族核心成员的压力之下,利用自己的权势得到正式制度的重要岗位,并集中关照少数人利益,打压异己,就与村霸无异。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假想中的乡贤与村霸即使放在当今时代,也不好简单区别。传统农业文明之下,特别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况下,村庄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单元。贫穷居民大多具有依附性,即在个人与宗法领袖的价值判断及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个人会服从宗法领袖。只要村庄保持一定的封闭性,现代要素不进来,官方腐败及匪患也没有渗透,这些宗法领袖就可以把乡贤一直做下去。
而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现代要素对村庄的渗透有快有慢,有浅有深,宗法领袖自己会发生蜕变。蜕变成功,可能就转化为现代乡贤;若不成功,要么自己被替代,要么自己变成村霸。究竟是变成隐蔽矫饰的村霸,还是明火执仗的村霸,则会受很多因素影响。
打破乡村“政社合一”体制
现代乡贤可以有,且可以与村霸势如水火,但前提是乡村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一是农民要富裕起来。生活富裕是减少依附性、向往自由的基础。为此要促进农村开放,给农民绝大的职业自由选择空间,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成为收入比较高的专业农户。特别要让穷人生活在城市,而不是苟活于乡村。
二是要推进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与盈利性经济活动相分离,坚决打破村庄一级的“政社合一”体制,让村干部依法只管公共事务,将发展经济事务交给农户或其自愿结成的组织。这个办法会让乡村干部的“权力含金量”大幅减小,对于防止隐蔽村霸产生有釜底抽薪之效。中央在这方面已经有部署安排,有关改革举措若能加紧推进,大局便会显著改变。
三是乡村自治体的设置要到合适层次,最好设在自然村或现在的村民小组层次上。这样做有利于将真正起作用的乡村精英更好地被吸收于主流社会之中,减少他们被边缘化的感觉。很多地方的经验证明,这个做法相当有效,中央也做了试点推广部署。
这几方面的发展改革虽具有根本性意义,但功效发挥会比较缓慢,解决急迫问题还少不了依法打击行动。
久拖不决的村霸作恶问题,往往与保护伞有关。在政府系统打击腐败,维护廉洁勤政风气,坚决清理村霸的幕后支持者,对于专项行动的成功,具有关键意义。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