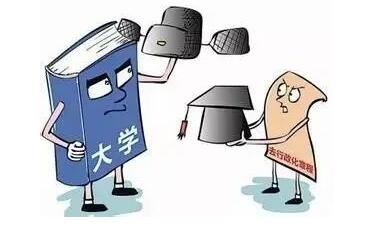《诗人的时代》
来源:上河卓远文化 作者:阿兰·巴迪欧 翻译:陈永国
在黑格尔之后的那个时代,在哲学常常与科学条件或政治条件缝合的时代,诗歌承担了哲学的某些任务。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个时代是特别为诗歌艺术准备的。然而,我们所说的诗歌和诗人既不是全部诗歌,也不是全部诗人,而是其作品即刻被认为是思想创造的诗人,对这些诗人来说,诗歌是语言的场所,是在哲学摇摆不定的地方提出关于存在和关于时间的命题的场所。这些诗人并没有决定取代哲学家的位置;他们没有清晰的意识要发挥哲学家的作用。相反,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承受着一种思想压力,即在哲学缺乏自由的情况下,需要在艺术内部构建接受思想的一般空间和类属规程,而这是被缝合的哲学所再也不能建构的了。如果诗歌特别承担了这项任务,那是因为:一方面,至少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哲学并不具备以某种特权方式被缝合的条件;另一方面,诗歌是把词语与经验相结合的一门艺术,距离现实较远,在空想的地平线上用词语表达此在的理想。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竞争可以回溯到古代,如柏拉图对诗歌和诗人进行的特别苛刻的检验。尼采充当了报复柏拉图的先知,而这种报复不可能在诗歌的权限之内进行。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完全可能会成为数学家、历史学家或物理学家,如果他们不可能是另一种人的话,那就是诗人。但是,自尼采以来,所有哲学家都声称是诗人。他们都嫉妒诗人;他们都是妄想型诗人或近似型诗人,或得到承认的诗人,如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或拉库一拉巴特,甚至詹贝或拉德罗都崇敬东方形而上学中不可避免的诗歌倾向。
事实上,在缝合的哲学家回转的时代里,确实有一个诗人的时期。在荷尔德林与保罗·策兰之间有一个时期,关于时代本身震撼人心的意义,关于存在问题的最开放的方法,几乎未陷入残酷缝合的共存空间,以及最丰富的关于现代人经验的论述,都在诗歌中释放出来,为诗歌所拥有。在这个时期里,时间之谜与诗歌隐喻之谜交织在一起,而解放的过程本身则与形象的“相像”密切相关。整个这个时代在短暂的哲学中再现为一致的,尤其是方向明确的一个时代。这些短暂的哲学包括进步、历史感、千年至福的基础、彼岸世界和他人的接近。而这个时代的真实状态则恰恰相反,是矛盾和混乱。只有诗歌,或“玄学”诗歌,最凝练的诗歌,最具思想性的诗歌,但也是最含混的诗歌,表达了这个时代本质的无方向感。诗歌在历史的定向再现中追溯出一个没有方向的对角。这些诗歌闪光的枯燥打开了一个空间——借用拉库一拉巴特从荷尔德林那里演化来的话,就是cesurer,“切开”的意思——即在历史性创伤内部切开一个口子。
一旦哲学试图与诗歌条件缝合,诗人时代的规范表征就成了哲学选择的客体。米歇尔·德古伊(MichelDeguy)甚至说(可他实际上是个诗人):“哲学,是为诗歌做准备。”无论如何,哲学所认可的诗人最终发挥了哲学自身的基本作用。
就我而言(但我认为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自己的名单就是从这个角度列出的,因此也是封闭的),我认可七位重要诗人,但不必因为他们是“最好的诗人”——一种不可能的奖项分配——而是因为代表着诗人时代的不同时期。他们是:荷尔德林,这些诗人的先知和预言家,然后是其他诗人,他们都是巴黎公社的后代,而巴黎公社标志着定向感所再现的混乱的开端:马拉美,兰波,特拉克尔(Trakl),佩索阿(Pessoa),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和策兰。
我不想有意检验这些历史性吻合,转变,奠基的诗歌,独特的成就(如马拉美的书,兰波的无序和佩索阿的异音异义词……),那么多概念而又不能联合成整体,正是这一点使诗人时代成为了思想的时代。然而,我还是要提几点意见。
(1)我们的诗人留下的一条基本路线,使他们能够摆脱哲学缝合的路线,就是缺乏客体范畴。确切一点说,是作为必要表现形式的客体范畴或客观范畴的缺乏。诗人时代的诗人试图打开的是存在之路,也就是存在无法通过客体的“表现”范畴来保护自己的地方。而诗歌本质上是抵制客体化的。这绝不说明意义已经转手主体或主观范畴。相反,诗歌所极其敏感的是缝合在“客体”或客体性与“主体”之间的纽带。这个纽带构成了知识或认知。但是,诗歌所尝试的存在之路并不属于认知秩序。它因此与主体/客体的对立构成了对角关系。当兰波激烈嘲讽“主体性诗歌”时,当马拉美提出诗歌的发生是作为主体的作者必须缺场时,他们说的是诗歌的真理并不在于它所说的是否与主体或客体相关。因为对诗人时代的所有诗人而言,如果经验的一致性与客体性密切相关,如同缝合的哲学依赖康德一样,那么,它就必须大胆地防止人们抨击它不一致,如策兰令人羡慕地总结的一样: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